从医院辞职,就像在中国脱离任何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一样。一张手续单上盖着来自人事处、财务处、保卫处、病案科、供应科、工会等共计 21 个部门的红色印章。医生王森才终于脱下白大褂,离开手术台。
在辞职之前,王森身心俱疲。他粗略统计,这些年由他担任主刀的手术一共 2000 多台,有他参与的手术不计其数。
「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,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。但重要的是,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。」
出生于 1982 年的王森,做了整整十年医生。他毕业于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医学院,获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,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王牌科室就职。
从实习医生、住院医师开始,他一年一年地熬过了年轻医生最艰难的时段,晋升为主治医生,成为科室中同年资最优秀的外科主刀大夫之一,今后本应是平步青云,一帆风顺。
可是他却放弃了。中国医疗环境的凶险和未知让他感到悲观,他声称自己看到了很多「黑暗的、隐性的东西」。
中国医生的收入与付出无法成正比
每一年的手术量要提高 10%。就是说不管上一年做到什么程度,下一年的手术量都要比前一年同期提高 10%。如果医生达不到指标,就扣除奖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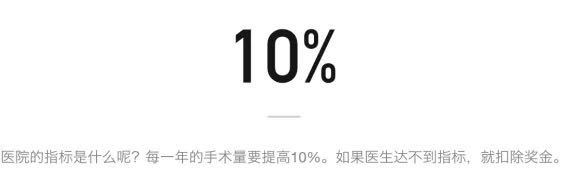
这样的结果就是,我要不断增加手术量,不断缩短病人住院的时间。
「以前一天做两、三台手术,后来增加到一天五、六台手术,甚至七、八台,这是我在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事实。没有人反抗,大家都逆来顺受,随波逐流。
就像北京的房价一样,最开始你觉得两三万一平米很贵,你觉得忍受不了,但是现在十万块钱一平米你也不得不买,你要继续忍受。」
中国,培养医生的成本高昂。一名医科学生成为执业医师,通常需要七至八年,成为主任医师需要约二十年。但医生所能得到的物质回报却不一定尽如人意。
中国的医疗服务定价很低。通常来讲,门诊挂号费、医生护士的诊疗费都只有几元到几十元不等。医生没有高薪。

做医生,基本上『五年一个台阶』。医学院毕业生,从业五年可以考主治医师,再过五年就可以考副主任医师,然后是主任医师。一个医生在 40 岁上下,职称就基本到头了。
不同职称的基本工资相差不多。我作为主治医师的底薪是每月一千元(人民币),主任医师也就比我多两三千块钱。剩下的都是靠奖金,奖金就是临床工作的提成、手术的提成,按照比例分配。
现行的医疗收费,绝大多数都是耗材的费用,而支付给医生的人工费用其实很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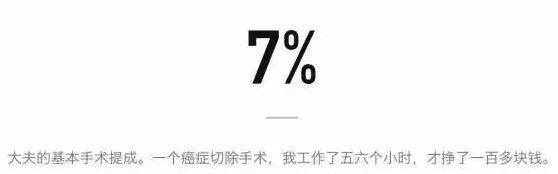
提高收入,就只有靠「灰色收入」
有一些是正常的灰色收入,比如去讲学,讲一次课能拿两三千块钱的报酬;
有一些是擦边的,就是走穴,比如医生外出会诊,到别的医院做手术。现在国家是默许走穴的。以我工作的领域来说,全国最牛的几个大夫,走穴做手术的行情是一万到两万吧。
另外一部分灰色收入就是回扣,药品和器械的回扣。

「回扣要分科室。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?因为确实很挣钱。心内科导管室做介入的也很挣钱。像我所在的科室这一块就比较少,没有什么耗材,有的也是『小钱儿』,放一个止血的、防黏连的器械,一次可以提几百块、一千块的回扣。」
「科研压力就像脑袋上悬的剑」
中国的医生,只有「白天忙临床、晚上忙论文」,才有可能在同行之中脱颖而出。
大医院里面的每天都是车轱辘一样地转,除非是特别差劲的,其实所有医生的指标(例如手术量)都差不多,没什么可比的。谁能晋升职称,谁不能晋升职称,说白了大家最后比的是科研,谁能发文章,谁能申请基金。
「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,是一个紧箍咒,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。就算置身事外,只做手术,不做科研。但到了发工资的时候,别人比我多挣几千块钱,总之心里还是会不舒服。」
「当了医生才开始学怎么和病人打交道」
医患矛盾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。
在中国,医疗服务被民众定义为消费。患者认为自己花了钱,理应有好的结果;一旦不如意,就会产生医疗纠纷。
中国的医学教育只重专业知识,忽略人文教育。王森感到,曾经的他作为一名医科学生,却对医者的社会属性没有足够的认知和理解。很多医生在从业过程中,只能向患者提供技术帮助,却忽略了人文关怀。
当然,医生的心理压力确实大,成天一大堆病人和家属围着,两分钟看一个病人,还有过来「加号」的,就不会耐心服务了,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。
但是患者作为「弱者」,通常更加容易被同情。医院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患者斡旋,也通常会以「息事宁人」的原则对家属以金钱上的抚慰。这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暴力冲突的发生。

医护的身体和心灵却很少被关注
而比起医生群体的流失,中国病人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。根据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,因为压力、不良生活习惯、环境污染等原因,中国的患病人口在激增,官方预测从 2000 年到 2025 年,中国患病人数将增加近 70%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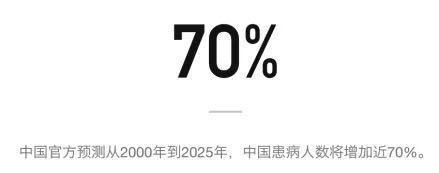
如王森一样的年轻医生包括护士群体,他们的工作量超出常人想象,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,却很少被社会关注。
「压力真的很大,有时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不负责任的,但是我没有任何办法。」
而且当了主治医生以后,不直接接触病人了。
其实第一次开皮、第一次缝肚子、第一次切除器官、第一次剔除肿瘤……其实只是暂时高兴一下,就过去了。真正给我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,还是有感情交流的病人,而不是「我能做什么」的成就感。
我还是选择了离开
「我在这家医院刚开始工作的时候,还是旧楼,墙皮都往下掉。后来医院的新楼越盖越多,大夫的工作条件还是那么差,所有的年轻医生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面,抢电脑、写病历。一个屋子里只能放 10 台电脑,有 40 个医生去抢。」
「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。能在国内做医生的人,就不会在乎工作环境有多差、工作强度有多大。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,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。
但重要的是,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。如果不符合,人就会很失落、迷茫,然后随波逐流。时间久了,负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,最终让我离开。」
丁香哥哥想和大家说,世上很多事,只有一个真正的值得坚持的理由,就抵得过无数应该放弃的理由。每一行都是有自己的苦楚,如果选择跳槽或转行,都是需要建立在良好的经济和资质基础上的,切不可盲目从众。
再次感谢,一直这么努力的自己。